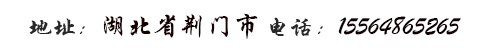都柏林,平凡的对立面纸城TRAVEL
|
白癜风症状 https://m-mip.39.net/nk/mipso_6947166.html 本公号属于经济观察报·书评 编辑/日京川 ?????? 我喜欢都柏林那些夜晚的忧郁,尽管它们沉重地压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夜晚的火车站总是悲伤难耐,当返回韦克斯福德的旅程开始,火车驶出韦斯特兰路时,我不得不把脸转过去,紧贴着车窗,不让我的母亲和姐姐看见我的眼泪。我现在看到的反射在镜子里的不是潇洒奔波的间谍,只有一个又哭又闹的小男孩,他的心里充斥着悲伤。也说不上为什么或究竟什么原因,我泣不成声,满是苦闷。我紧握拳头、闭紧嘴巴,防止不自觉地发出啜泣声,但现在回想起来,我想那是因为有些东西正在结束,像马戏团的帐篷那样,正在被折叠起来。简而言之,它们正在成为过去。—约翰·班维尔都柏林从来不是我的都柏林,这使得它更加诱人。我出生在韦克斯福德(Wexford),那是一个小镇,当时比现在更小、更偏远,它的过去不为外人知晓。我的生日是12月8日,在圣灵感孕节(theFeastoftheImmaculateConception)那一天——我一直把这事作为一个例子,说明上帝在弄混出生日期这个问题上,实在是不太精明、太过荒诞。8日常常既是宗教节日又是公休假日,来自外省的人们纷纷涌向首都,做圣诞节采购,同时,他们对都柏林的圣诞灯饰惊叹不已。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的前五年,我的生日乐事都是乘火车去都柏林,这件事我事先会盼上好几个月——事实上,我怀疑前一年的短途旅行一结束,我就开始期待下一年的旅行了。我们将在冬日清晨的黑暗中从镇上的北站启程。我相信当时仍然有蒸汽火车,虽然柴油机车已是新事物。在昏暗和空荡荡的街道上行走多么令人激动,我的脑袋还因为没睡醒而恍恍惚惚,而等在我面前的是一整天的冒险。火车将从罗斯莱尔港(RosslareHarbour)驶来,运载着从威尔士的菲什加德(Fishguard)来的夜班渡轮,走下来的乘客目光迷离,其中一半喝醉了,另一半表现出晕船的症状。我们将乘着火车咔嚓咔嚓地出发,我旁边的窗户像一面昏暗的玻璃镜子,我可以从里面端详自己阴森的映像,想象自己是一个秘密特工——在过去的间谍小说中,常常这样称呼间谍——登上了东方快车,身负绝密使命,前往黑暗而危险的东方。我们会来到接近阿克洛(Arklow)的某个地方,这时黎明来临,霞光将霜白色的田野变成一片亮闪闪的云母粉色。某些地方的某些时刻,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带着奇异的生动和清晰,印刻在我们的记忆中。奇异是因为,它们如此清晰、生动,以至于人们怀疑一定是他们的想象力把它们编造出来的:一句话,它们一定是人们想象出来的。在那些12月的旅行中,我记得,或者我确信我记得,火车在河湾的某个地方慢下来——那一定是阿沃卡河(Avocariver)——在我的记忆之眼中,我仍能清晰地看到这个地方,而且我的小说中也多次出现了这个地方,比如在《牛顿书信》(TheNewtonLetter)中,摘录如下:在河的那一边,有一片平坦的田野延伸至一座树木繁茂的小山边缘,山脚下有一幢房子,房子不太大、孤零零的、四四方方,屋顶很陡。我会凝望那寂静的房子,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想知道那里面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谁堆放起柴火,挂起那冬青花环,在山上的白霜中留下那些足迹?我无法表达那一刻的快乐,奇怪,又令人心痛。当然,我知道,那些神秘的生活和我自己的生活不会有太大的不同,但这才是要点。我追求的并不是异域风情,而是平凡的人或事,那种最奇特、最难以捉摸的谜团。 当然,都柏林是平凡的对立面。都柏林对我来说,就像契诃夫的《三姐妹》中的莫斯科对于伊琳娜一样,是一个充满魔力的应许之地,令我饥渴而年轻的灵魂永远向往。我比伊琳娜幸运,因为从韦克斯福德到都柏林的路程相对较短,只要我想经常去,就能如自己所愿。在贫穷的20世纪50年代,这座城市本身,也就是真正的都柏林——基本上是一个既没有吸引力又难看的地方,但是这并没有磨灭我对它的憧憬,甚至当我身处其中的时候,我也热望着它,以至于平凡的现实在我眼前不断地转换成超乎寻常的浪漫。没有人比一个小男孩更浪漫的了,正如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LouisStevenson,—),19世纪后半叶英国伟大的小说家。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金银岛》《化身博士》等。早年他到处游历,为创作积累了资源,后期致力小说创作,取得了极高的成就。——译注,后文皆同。比大多数人都更明白的那样。……O’ConnellStreet,.过去是从什么时候成为过去的?那些以前仅仅是发生的事情要过多久才开始散发出神秘和超自然的光芒,标志它们已经真正成为过往了呢?毕竟,我们记忆中承载着的辉煌幻象,一度只是现在,平淡无奇、枯燥乏味、完全不值一提,除了一些时刻,譬如一个人刚刚坠入爱河、中了彩票,或者听到医生传达坏消息的时候。当我们把经验送进过去的实验室,是什么样的魔力才将其塑造和打磨出最后背影,珀西广场段大运河所呈现的光辉?这些问题都只是一个问题;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它们就让我着迷,那时,我第一次有了一个巨大的发现,即创造物不仅包括我和我的附属物——母亲、饥饿、偏爱干燥甚于潮湿等——而是,一方面包括我,另一方面也包括世界:由其他人、其他现象、其他事物组成的世界。这么说吧,现在是我们生活的地方,而过去是我们梦想去往的地方。然而,即使它是梦,它也是坚实和持续的梦。过去是一个用绳子拴住和不断膨胀的热气球,使我们在空中飘浮。然而,我再问一遍,过去是什么?现在必须经历什么样的嬗变才能成为过去?时间的炼金术在一个明亮的深渊里暗自蓄力。……韦斯特兰路车站(WestlandRowStation韦斯特兰路车站(WestlandRowStation)——多年以后,它才变成皮尔斯车站(PearseStation)——基本上是一个巨大的被煤烟熏黑的玻璃穹顶,几座阴冷的站台,以及向下通往街道的斜坡。现在我才察觉,以往的12月8日,我们每次到这里时都在下雨。它并不是外省猛烈的暴雨,圣安德鲁大教堂,韦斯特兰路而是只有在城市才能见到的那种,它的雨滴像中微子一样,细小又有穿透力,那些大批倾盆而下的亚原子,实际上是比亚原子还要小的粒子,在每一个瞬间快速穿过你、我和所有事物。这样的雨水与其说使人行道变得潮湿,还不如说使它们变得湿滑,所以人们脚踩滑溜的皮革鞋底在上面行走时,必须小心谨慎。肯尼迪酒馆(Kennedyspub)在街道的尽头,过去有——现在也有——一家肯尼迪酒馆(Kennedyspub),萨缪尔·贝克特萨缪尔·巴克利·贝克特(SamuelBarclayBeckett,—),爱尔兰著名作家、评论家和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年毕业于都柏林圣三一学院,获法文和意大利文硕士学位。他以创作荒诞派戏剧闻名,代表作品有《等待戈多》等。在附近的都柏林圣三一学院读本科时经常在此喝酒。左转弯,然后马上右转,我们将进入梅里恩广场(MerrionSquare),那里的一号楼是乔治王时代艺术风格的有露台排屋的建筑典范(至少在外表上看是如此),奥斯卡·王尔德即出生于此。他的父亲是威廉·王尔德(WilliamWilde),一位“杰出的医生”,就像人们过去常说的那样。奥斯卡的母亲是出了名迷人的简·弗朗西斯卡·王尔德(JaneFrancescaWilde),她的娘家姓埃尔吉(Elgee),她在19世纪40年代以笔名斯佩兰萨(Speranza)为“青年爱尔兰”(YoungIreland)成员所办的报纸《民族报》(TheNation)撰写爱国诗歌。她的诗如此激动人心,以至于在某个动荡的时期,她差点被指控煽动叛乱,投入监牢。简·弗朗西斯卡·王尔德(JaneFrancescaWilde)我几乎不需要说,在我正在记述的那段时间,我对那些事情一无所知。我怀疑我当时甚至没有听说过可怜的奥斯卡,而今天有一座造型极其丑陋、着色俗不可耐的雕像纪念他,雕像中的他正不合礼节地躺卧在栅栏后面的一块岩石上,位于他诞生地的对面广场的一角。我们竟认为我们可以自由地拜访逝去的名人,这是何等的侮辱!我们以萨缪尔·贝克特——这位最热爱和平的人——的名字命名一艘炮艇,而《尤利西斯》的零星片段,用浮凸字体雕刻在微型黄铜板上,嵌入都柏林的人行道,供大家踩踏。我在这里停下来惊奇地思索,在几个世纪里,很多事情都是相互联系的,尽管这种联系太过微弱,却令人惊讶不已。简·“斯佩兰萨”·王尔德的父亲是韦克斯福德的一名律师,而不久前我在巴黎投宿的酒店房间,正是她的儿子奥斯卡最终断气之所,当时他因为债务不堪重负,同时抱怨着糟糕的墙纸。世界是偌大的一个地方,但有时似乎的确小得令人起疑。大运河(GrandCanal)猝不及防,在回想起巴格特街桥时,我停顿了一会儿,细想北向的风景——是北向的吗?——沿着大运河(GrandCanal)一直到休班德桥以及更远。我想,我们所有人心中都有一个特殊的地方,那是一个私人的天堂,如果我们死后必须去一个地方,我们都希望是那里。对我来说,从巴格特街下至下山街(LowerMountStreet),那片宁静的水面、沙沙作响的芦苇和深棕色的纤道,是我知道的最可爱的水景,甚至胜过意大利威尼斯的大运河,虽然那里有用柔和的颤声歌唱的贡多拉船夫。我从最早的时候开始就知道巴格特奥尼亚地区(Baggotonia)——当地居民如此亲切和自豪地称呼它——而且,最终我还无比好运地住在那里,度过了我认为必须视作我的“性格形成期”的那些年。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较幸运的福分之一。……《一个英国瘾君子自白》 (ConfessionsofanEnglishOpiumEater) “天才,”波德莱尔评论说,“无非是精确阐述的童年。”我相信,这位伟大的法国颓废派艺术家——他在这里评论的是同样颓废的英国散文家托马斯·德·昆西(ThomasDeQuincey),《一个英国瘾君子自白》(ConfessionsofanEnglishOpiumEater)的作者——打算让“天才”一词在这个语境中被理解为“守护神”。古希腊人相信它存在于每个人身上:他的性格,甚至他的本质。如果波德莱尔是正确的,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童年从未终结,而是存在于我们身上,不仅仅是作为记忆或记忆的复合体,而是作为我们内在本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个艺术家都知道这一点,因为对于艺术家来说,童年和童年时对事物的概念,是常被称为灵感的东西的深层来源:原因之一在于我们尚是孩童时,第一次把这个世界看作神秘的事物。可悲的是,长大的过程是把神秘变成平凡的过程。我们不再对事物感到惊讶——天空、四季变换、爱情、其他人——只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它们。设想一个来自与我们完全不一样的遥远星球的人,他的政府正不怀好意地考虑长期占领地球的可能性,他被派到这里全面考察地球及其居民,然后向政府汇报。他快速地侦察四周——他具有快得惊人的观察、吸收能力——他正在对他的报告做最后润色,这时开始下雨了:水,从天上落下来!或是有人打喷嚏,这突然发作的是什么?或是有人打哈欠,这无声的尖叫是什么意思,而且为什么周围的人们对这种景象不感到惊讶和恐惧?我们的外星人当场意识到,他将不得不撕毁并重新起草自己的报告,因为这个地方远比他最初认为的要奇怪得多。孩子,就像那个收集情报的外星人一样,存在于一种不断重复发生的惊讶状态——每隔一刻,他就会遇到一些不同寻常的新事物——但是最终他的感觉变得模糊了。不幸的是,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某一时刻到了,他见识了一切。但我们没有人见识过一切:一切如新,每一次都是第一次。我们不是长大,我们所做的只是变得迟钝。所以,在春天潮湿的天气里坐在这儿写这本准回忆录的七旬老人,也是在很久以前12月的某天,饱食了香肠、咸肉薄片和凯勒莫尔蛋糕后,乘坐10路公交车前往市中心——或者说AnLár爱尔兰语,意为中央。,就像公交车前面的说明指示牌写的那样——的那个孩子。我回过头来,看到一个七岁的陌生人,但他又是我。可那怎么可能呢,我是那个孩子,那个孩子是我?这个问题萦绕在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心头,他把它与其他类似的难题相提并论——玫瑰在黑暗中是红的吗?如果狮子能说话,我们能听懂吗?——他尝试过,却未能解决这些难题,令人着迷的失败。**在格拉斯内文植物园的棕榈屋里有一块牌匾纪念维特根斯坦。20世纪40年代末,这位哲学家住在都柏林,在那里他有一个好朋友——莫里斯·德鲁里医生(Dr.MauriceDrury),医院的精神科咨询医生。维特根斯坦投宿于罗斯旅馆——现在的阿什林旅馆——那里有他的另一块纪念牌匾,他在比尤利餐厅或动物园的议员餐厅吃午饭,有时坐在棕榈屋温暖的台阶上工作。一个人老了之后,和他还是小孩的时候,他们是同一个人吗?在我的眉间有一块小小的白色锯齿状疤痕,那是我四五岁时遭遇一次不幸事故后留下的。有一天,在我出生的韦克斯福德,我跑过信仰广场(Faythe),那个名字相当古怪的广场——实际上它是楔形的——撞在一个边缘锋利的木桩上,它支撑着一棵新栽种的树苗。几年前,我回到信仰广场去看看那老地方,惊奇地发现那里有一片茂盛的成熟树林。我感到困惑,因为在我看来,它们似乎已经站立了好几个世纪。“啊,不,”我姐姐轻轻地告诉我,“它们的年纪只差不多和你一样大。”我惊呆了,用手指摸了一下额头上的疤痕,心想:当这些树被栽种的时候,我就在这里的,我活生生地在这里!像华兹华斯声称的那样,儿童是成人之父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晚年有这种想法,即出生伊始的孩子竟是自己多年后的父亲,这不是荒诞不经的念头吗?过去什么时候成为过去?……奥康奈尔街(O’ConnellStreet)奥康奈尔街(O’ConnellStreet)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它的鼎盛期,后来它变成了拉斯维加斯一条较肮脏和偏僻的霓虹灯带的复制品。当时,那里生长着真正的树木,英国梧桐,其中一些可追溯到19世纪。十年前,它们被全部清除,取而代之的是矮小瘦弱、毫无特色的植株,看上去好像是塑料制品。纳尔逊柱(Nelson‘sPillar)仍然屹立,雄伟但不协调。公交车沿着街道两旁隆隆行驶,像大象一样吼叫着,车身涂成苔藓绿色,车内后部有一个敞开的平台,当车辆起步或颠簸着停下时,人们可以忽略售票员疲惫的重复警告,抓住一根光亮的银色杆子,惊心动魄地跳上跳下。有一天,我目睹了一位女性化的年轻人,像过圣诞节一样穿得稀奇古怪,当公交车停下来时,他像跳芭蕾舞一般迈下其中一辆。汽车停稳后,售票员——一个身材矮小的家伙——出现了,挥舞着一把收拢的雨伞。“嘿,仙都柏林尖塔(TheSpire),奥康奈尔街女!”他在正要离开的花花公子身后讥讽地叫道,“你忘了你的魔杖!”年轻人停下脚步,转过身,走回去,接过雨伞,用雨伞的顶部轻敲奚落他的人的肩膀,说道:“变成狗屎,邪恶的侏儒!”在那些不太理解并包容同性恋的时代,同性恋者真是幽默源泉,令我们捧腹大笑。格拉夫顿街(GraftonStreet)有“斯维茨尔”(Switzer)和“布朗·托马斯”(BrownThomas),但这些高端的顶级百货商场是给富人用的;我们这些多少属于下层社会的人,不得不满足于奥康奈尔街的“克利里”(Clery)。“克利里”肯定是这些岛上最大的百货公司之一,有很多楼层,数英里长的柜台,透着无法遮掩的破旧气息,但我们也乐意接受。我记得光秃秃的地板,但是这一点我一定是弄错了,因为那儿至少会有油地毡。这家商店的男性员工主要是中年男人,他们分为两种:有些人十分有趣,擅长讲些有伤风化的俏皮话——“这松紧带经久耐用,夫人!”;还有些思想不集中的,看上去似乎还带着些许绝望的人,我觉得他们的样子像是有教养的囚犯,正在急切地期待能因表现良好而早日获释。他们的女同事穿着黑色衣物:黑色的裙子、黑色的套装毛衣、高度适中的黑色皮鞋。她们动作麻利、称职能干,有几分殉道者的风范,活像一群世俗的修女在操办修道会。我们的第一站是珠宝部,每年母亲都会在那里为我买一只16便士的手表作为生日礼物。这些小计时器令我陶醉、让我着迷:它们的皮带有财富的气味,据说它们的内部机件中嵌有红宝石——真正的红宝石!我们买得起的那些是属于这系列产品中相当低端的产品。如果我够走运,到第二年年初,它们还能分秒不差,然后就没法控制自己的速度,要么似乎疲惫不堪地走得极慢,要么提前几个小时,狂热地嘀嘀嗒嗒走得飞快。当它们终于寿终正寝后——这通常在二月中旬——我又会偷偷从我母亲梳妆台的抽屉里借用她那块优雅的欧米茄小手表,因为让我在同学中间像一个穷光蛋露出光秃秃的手腕是不可想象的。格拉夫顿街(GraftonStreet)购买手表的仪式结束后,我要忍受一段枯燥乏味的时间,没精打采地跟在我母亲、姨妈和姐姐的后面,看她们忙着做当天最主要的事情,购买在我看来沉闷得无可救药的圣诞礼物。百货公司的衣架上很少有能让一个小男孩高兴的东西,即使他有一只闪亮的新手表可以炫耀。没错,他可以向紧身衣销售部的人体模型抛媚眼,还可以仿佛不经意地用手背掠过一架子凉爽而脆硬得令人兴奋的尼龙衬裙。他也可以幻想凯瑟尔·邦多尔女士——“女式贴身内衣裤!家常服!胸罩!”——匆匆把他带走,他满心喜悦,克里利百货公司的门牌,奥康奈尔街毫不反抗,任自己被掳到她的闺房。这个可爱的尤物,画在一个直立的硬纸板牌子上,是一位身材高挑、杨柳细腰、嘴唇深红的美女,不知羞地展示着她长筒袜的上部,以撩人的姿态在我童年时代的许多幻梦中大摇大摆地走过,当我在过往悸动的回忆中想起她时,她甚至——或许可能为了我好、为了挑逗我——抖动着她那匀称的腿。**在互联网遥远的星系中,仍然可以看到她在闪烁,像往常一样身着华丽长裙,摆出各种优雅的引人遐想的姿势。款待、款待、更多的款待。在奥康奈尔街,至少有两家冰激凌店,“百老汇”与“棕榈滩”——我听说餐厅评论家保罗·图利奥(PaoloTullio)的家族拥有其中一家,或者也许两家都归他们所有——毫无疑问,在某些人眼里,它们是廉价和俗气的场所,但对我们来说,它们就像加州一样多姿多彩。我更喜欢“棕榈滩”,为了它极好的“荷兰裔纽约人荣耀”冰激凌——我仍然可以看见它闪闪发光的深红色糖浆,沿着玻璃杯的侧面,呈蛇行运动,更确切地说像蜗牛一样慢慢滴淌下来——为了它的“忧郁宝贝”,以及听起来越发不得体的“香蕉半剖条”。奇怪的是,我只记得被我哥哥带到那里,那时他是个十几岁的少年,而我还在穿短裤。是我想象的呢,还是“棕榈滩”上确实每张餐桌旁都有一台投币的自动点唱机,你可以投入一枚硬币,然后选择一首最喜欢的曲子?我哥哥欣赏当时较为高雅时髦的流行歌手:弗兰克·辛纳特拉(FrankSinatra)、多丽丝·戴(DorisDay)、佩里·科莫(PerryComo)、纳特·金·科尔(NatKingCole)、罗丝玛丽·克鲁尼(RosemaryClooney)、墨迹斑斑乐队(theInkSpots)、特丽莎·布鲁尔(TeresaBrewer)……音乐!音乐!音乐!在那些漫长的生日时光中,除了在南姨妈单元房里吃早餐,下午晚些时候在雨水冲洗过的奥康奈尔街吃杯用高脚玻璃杯盛的冰激凌,我一定还吃过其他东西。也许在艾比街的温斯酒店吃了午餐——我们称之为正餐,经常出没在那里的有喝着威士忌、大声喧哗的神父,还有头戴软毡帽的形迹可疑的人,以及形只影单、满眼憧憬但不再年轻的女士,穿着有缝长筒袜和华丽的上衣,坐在吧台,面前摆一杯杜松子酒加“汤力水”汤力水(TonicWater),最初作为药物使用,后成为热门的鸡尾酒配方。,指间夹着一支香烟,香烟的唇端染成了红色,以别致的角度出没在没戴戒指的左手指间,格外引人注目。餐厅里,在被烟草烟雾熏成忍冬黄色的天花板下,“正餐”将是一碗米黄色的汤,接着是一个灰白色的大盘子,上面扔着两三片灰褐色的厚牛肉,一旁的蔬菜煮得几乎毫无生气,丝毫不见原先绿油油的模样,上面涂了层像蛋奶沙司的某种东西,再来几杯茶水(那茶水的颜色像在沼泽水中淹没了好几个世纪的树干),整个用餐才算圆满——或者说“才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正如乔治·奥威尔说的那样。12月接近圣诞节时,白天很短,结束时有一种软软的虚脱的感觉。我喜欢都柏林那些夜晚的忧郁,尽管它们沉重地压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夜晚的火车站总是悲伤难耐,当返回韦克斯福德的旅程开始,火车驶出韦斯特兰路时,我不得不把脸转过去,紧贴着车窗,不让我的母亲和姐姐看见我的眼泪。我现在看到的反射在镜子里的不是潇洒奔波的间谍,只有一个又哭又闹的小男孩,他的心里充斥着悲伤。也说不上为什么或究竟什么原因,我泣不成声,满是苦闷。我紧握拳头、闭紧嘴巴,防止不自觉地发出啜泣声,但现在回想起来,我想那是因为有些东西正在结束,像马戏团的帐篷那样,正在被折叠起来。简而言之,它们正在成为过去。本文由出版社授权转载,节选自《时光碎片》第一章关于时间部分内容 《时光碎片》(爱尔兰)约翰·班维尔/著金晓宇/译南京大学出版社年11月巴黎之于海明威,是一场流动的盛宴,都柏林之于班维尔,同样如此:乔伊斯、叶芝、贝克特等纷聚于此,在都柏林寻找自己的文艺梦。在班维尔的引领下,一场奇妙而独特的都柏林之旅就此铺展,重回那个充满文艺气息的黄金创作年代,游荡于此时彼刻的都柏林的文化、建筑、社会、历史、班维尔的文学交友记忆与创作现场……作者简介:约翰·班维尔(JohnBanville)爱尔兰著名小说家、编剧。年出生于爱尔兰韦克斯福德。班维尔的小说以精准、冷酷、充满辩证的散文风格著称,同时兼具纳博科夫式的创新。他的主要作品有《哥白尼博士》(年布莱克纪念奖)、《开普勒》(年《卫报》小说奖)、《牛顿书信》《证词》(入围年布克奖短名单)《幽灵》《雅典娜》《裹尸布》等。年,凭借小说《海》获布克奖。年,获弗朗茨·卡夫卡奖。近年来,班维尔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者之一。纸城君拉你入群点击标题查看以往精彩内容 “我这辈子都在迷路啊” 纸城CHAPTER 菲利普·罗斯:文学生活的捍卫者 纸城REVIEW 范妮娅·奥兹:我们知道的只是过去,因此是倒退着走向未来 闲散不是懒惰,而是一种抵御实用的态度 纸城MODERN 咖啡馆如何搅动了文学、思想和阶级? 纸城PICK 如果暂时放下手机,你会发现我们依然生活在“旧世界”之中 那些无所不在的乏味影像,成为了真实生活的负担 在真实的世界里,任何成功都潜藏着失败 纸城PICK 不“吵架”的年轻人是没有前途的 纸城PICK 那些真正与我们有关的事情,在话语的阐释中蒙上了灰尘 音乐来自网易云音乐,版权归原作者 图片来自google,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投稿及合作邮箱:chenliping eeo.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falanxibaoa.com/flxbjj/5506.html
- 上一篇文章: 都柏林的时光碎片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