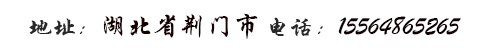两个肮脏的人谈了一场最干净的恋爱
|
▼ 朗读|温凉、诗皎,剪辑|诗皎 配乐|ArvoPa?rt-CantusinMemoryofBenjaminBritten, Miha?lyVi?g-Valuska 画|诗皎 巴黎腐烂就腐烂吧 文|温凉 打桩机在响,天空裂开一道缝。 云是馊的,阳光结成了痂,糊在大地上。 那个名叫亚历山大·奥斯卡·杜彭(AlexanderOscarDupont)的糟老头露出油肚皮,横卧在桥堡上,或许是我吧。 他嘴巴一张一翕,正吐出昨夜胃里没消化干净的芜菁、酸块菰、洋葱与艾尔酒。塞纳河正在维修,新桥暂不通行。 一只老鼠在我的呕吐物里爬动。川流不息的人们,形色匆匆,像白痴一样上班、下班、上班、下班。 他们上班只是为了下班。 我他妈喝多了,不是头一回了。有天夜里我躺在大街上,被呼啸的汽车压断了右腿。我就这样一步一步爬进救济站,被那群婊子养的像尸体一样拖来拖去。将我登记在册,拍大头照,按下手印,接着是没完没了的盘问。据说这是为了防止福利欺诈,可让我觉得,正是他们发明了贫穷本身,并把它定为一项新的罪行。 所有的伟大的法兰西公民们必须学会如何使用表格来逮捕自己。 于是,我将名字的字母重新排列,才有了现在的名字:莱奥·卡拉克斯(LeosCarax)。 我是在那年夏天遇上她的。她是个盲女孩,左眼看近物时会如同蜗牛般凸起、膨胀,而右眼常常溢出脓水。一身粗麻布涂满了渍痕。她喜欢画画、喝酒,神采飞扬。跟她在一起,让我觉得生命很美。 我们一起捡烟抽、偷酒喝、大笑、大醉、嘶叫、乱舞,跛着脚奔跑,在水里拥抱。塞纳河的一半是烟火,一半是我们。 我偷来一部16毫米的摄影机,发誓要拍一部有关她和我的电影。 直到我看见她父亲寻她的启事,才明白她是“上等人家”的女儿。为了与她永远厮守,我烧掉了她父亲贴出的所有海报,将骗来为她医治眼睛的钱撒进河里。 只有成为真正的弱者,她才离不开另一个弱者。 她的眼睛一天坏似一天,无法看清周遭细小的动作,几乎瞎了。为了让她看到我,我从此不再微笑,而是狂笑,我不再走路,而在人群中翻滚。我每天支付着我卑微的绝望,我可以为她入狱,为她而死,为她付出一切。 我爱你!但我禁止你离开我,去得到真正的幸福! 我是酒精喷薄的烈焰,而她是感光失灵的烟花。 她失明前的最后一个愿望是将一幅油画再看一遍。在午夜的卢浮宫里,她踩在我的肩上,我高擎着烛火,她那玻璃质地的空眼球已无法辨物,便用手指一寸一寸地“看”每道笔触的凹凸。就在那幅画前,我们紧紧相拥,我用黑暗苍凉的幕布盖住了她,烛光与她眼中最后的余火同时熄灭。 我因纵火罪而锒铛入狱。她自此盲而无依,白天在街上晃,晚上睡在下水道里。她被流浪汉们轮番殴打、强暴、酗酒、停经,变得不堪一击。她死的时候才33岁,但看上去有50岁,像一只瘦骨伶仃的塑料袋。是我亲手把她的尸体扔进河里的。就在那儿,那座她喜欢的桥上,我用偷来的枪打穿了我的左手掌。 如今我老了,兜里时常揣着上百枚钥匙,却什么也打不开了。 我当了一辈子的警卫,呆过工厂、大楼、灯塔、坟地,最后,成了这座桥的守门人。 桥连接着左岸与右岸,却分割着上流与下流。道理一样。 你可以依赖你的导盲犬,但永远不会对它产生爱情。这个社会的穷人和富人并非同一个物种。他们之间无法真正相爱。 阶级本是人类创造的概念,人反而借此画地为牢,相互划分,激起盲目的仇恨、莫名的恐惧,稀里糊涂的活,不明不白的死。 贫穷成为我一生无法克服的身份,我的梦想就是有生之年在我的电影里杀死它。 “那是我吗?” “是的,来自记忆。” “你哪里见过我?” “我以为你死了。” 一个半盲的女孩,一个跛脚的癞子,当年的事就要重新开始。 每个童话的开头都是“很久很久以前”,而所有谎言的结尾则是“一切不再遥远”。 而这一切,是献给所有住在桥上的恋人们的。 EyeLoveYou 你看见了所有的,我看见了唯一的 影片链接: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falanxibaoa.com/flxbzx/5960.html
- 上一篇文章: 法国砾石堡红酒来自梅多克的礼物二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