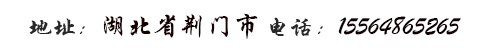叶书宏马尔克斯爱情和其他魔鬼爱可以战
|
———万物都和爱有关,献给浸在泪水之中的人们 “凡是幸福无法治愈的,任何药物也都无法治愈。” 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爱情是什么?在《爱在瘟疫蔓延时》中,它是一场无药可医、肝肠寸断的霍乱,在《爱情和其他魔鬼》中,它是一个摧毁信仰、在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前也不退让半步的魔鬼。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西印度群岛卡塔纳赫(今位邻南美洲委内瑞拉北岸),身为日报社记者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涉足一所正在被挖掘整理的修道院,后者早已在世界记忆的沼泽中被岁月抹去,只留下残垣断壁和具具被时间啃食尽血肉的白骨,等待着被新的纪元改造成五星级酒店。 在这些曾长眠于修道院灵龛中的骨骸中,一束古铜色的头发从挖掘的孔穴中露出来,足足有二十二米长,长发连着一个小女孩的头骨,为了来此地挖掘新闻的记者马尔克斯警觉到,骨骸极有可能属于一段过往传说中一位侯爵的千金,在记者从外婆那里听来的故事里,一束铜色的头发托在她的身后,宛如新娘的纱裙,在她十二岁时,被野狗咬了一口,因疑似得了狂犬病被送入这所圣克拉拉修道院,直到不久后过世,她再也没有看到过外面的世界。 加西亚?马尔克斯沿着这个传说的线索继续挖掘,最终还原了几个世纪以前,一段有如地狱中禽鸟般悲鸣的爱情故事。 在那个西班牙女王和天主教宗教裁判所还统治着这个被遗忘的遥远世界的时代,女孩的父亲,堂伊格纳西奥?德阿尔法罗侯爵,与他没有封号的妻子贝尔纳达?卡布雷拉产下一个刚出生就被父母亲遗忘的女孩——席尔瓦?玛利亚,她从小就被放弃责任的父母放养在府邸里黑奴脏乱生活、从事鸡奸和乱性、膜拜异教偶像的简陋屋棚中,不会读写,却能流利的熟悉每一种非洲语言和他们的魔鬼,她的父亲伊格纳西奥侯爵,根本不知道她已经长大到十二岁,他的母亲贝尔纳达则希望这个有魔鬼眼睛的孩子赶紧死掉。 在城里流行狂犬病的那段时间里,席尔瓦?玛利亚被一只因病发狂的疯狗咬了,在人们对这个不治之症的恐惧与流言蜚语中,侯爵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对这个生命无可抹除的责任和爱,他在对女儿命运的不安中去探视了因发狂而被关押在修道院的狂犬病感染者,惊恐和悲怆的见证了他们无边的痛苦,也清楚那个时代对于狂犬病,正派的基督徒唯一能做的,便是在自己不幸感染的家人发狂变成狗前悄无声息的毒死他们,这是宗教严苛的时代留给绝望之人的最后仁慈与拯救。 而对女儿迟来的认识和爱让侯爵做不到这一点,普通的一直深爱家人的人,在他们走到被发狂征服的时候,不忍让他们仍受痛苦,因为人们不能承受那些被我们爱的人受苦,而侯爵对女儿的爱才刚刚来到,他不允许命运就这样立马收走这份迟来的仁慈与天赋。 在症状发生前,忧心忡忡的侯爵在对宗教离经叛道的医生阿布雷诺肖那里接受了以幸福来治愈席尔瓦?玛利亚的建议,他企图一步步走进这个他从不了解的女儿,给予她迟来的父爱和陪伴,教她像一位真正的白人贵族那样生活,他甚至计划了陪女儿远赴塞维利亚的旅行,但也就是出发前的那一晚,女儿表现出了最无可争议的狂犬病征兆。 当晚,侯爵带女儿一起晚祷,他才惊讶和绝望的发现,自己唯一有机会尽的父亲的责任,却只能是帮女儿面对死亡。 “用我们俩的贱民换她的命,婊子。” 当晚侯爵走到妻子贝尔纳达的房间门口时,他这样说。 在这桩注定貌合神离的无爱之婚中,伯爵和贝尔纳达都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早就生存在狂犬病一般发狂的潜伏期中,贝尔纳达在对情夫犹达斯?伊斯卡柳特的爱情中坠入欲望和致幻剂的深渊,他和侯爵的婚姻只是资产阶级新贵想要挤入有头衔的贵族圈子的苍白结合,犹达斯的意外历史把这个曾经美丽的女人变成了一个腹泻失尽、对生活万念俱灰的丑陋胖子,而侯爵的心里则住着他的初恋——杜尔斯奥利维拉,他曾经不顾一切的爱过这个被关在疯人院里的姑娘,婚姻变成了逼疯各有所爱又又痛失所爱的两个陌生人的枷锁,而这疯狂的潜伏期相比于比狂犬病则长的太多。 侯爵开始求助于一切可能哪怕是可能存在的办法治疗女儿的狂犬病,庸医、邪教的巫师、药剂师、江湖郎中纷纷尝试,也都毫无办法,最终他把女儿送进了“无法拯救她的生命,却可以拯救她的灵魂”的圣克拉拉修道院,从此直到席尔瓦?玛利亚死去,都再也没有从这个名副其实的地狱中出来过。 在那个对疾病和对科学同样陌生的时代,狂犬病或者一切导致人丧失认知能力和精神发狂的症状,都被归类为魔鬼的附体,当地教区主教也正是也只是听闻了侯爵女儿感染狂犬病,就执意制定了她最后的归宿,对于他来说,其实病患在基督的圣所内不治发狂,也强过在摧毁信仰的异教徒诊断下康复,在那个时代里,真正死于病情的病情的,数量远远不必那些惨死于愚昧残忍的驱魔仪式的,有时候我们常常把某些我们搞不清的事情归结于魔鬼在作祟,而不去想,会不会是我们对上帝的理解还不够深刻。 席尔瓦?玛利亚在不能被确定会到来的死期来临前就提前下了人间地狱,被关在这所实则为疯人院和堕落者监狱的修道院中。本身就在无人疼爱、无人保护的环境下成长的席尔瓦,在这所屎尿满地、人心险恶的修道院中当然表现出对死亡的最后抗拒的恐怖,结合她遭放养以及和黑人共生而对生活形成的反常看待和习惯,想要撵走这个恼人责任的修道院自然真的把她视为带来一切不幸和灾祸的魔鬼。 而古板顽固的主教,一心要驱除附上她的地狱恶魔,这是他认同自己为这个充满鸡尖、偶像崇拜和嗜食人肉的遗忘之境牺牲一生的最后理由和安慰,他派遣自己的学生徳劳拉神父担任给这个女孩驱魔的神圣职责,而后者在第一次见到这个女孩时,在充满破败和恶臭的房间里,他们疯狂的相爱了。 驱魔的人反被魔鬼附体的人传染上了魔鬼,对于徳劳拉神父,这个魔鬼正是爱情,他一夜又一夜想着牢房里的女孩席尔瓦,他拷问自己的信仰,与确认女孩被魔鬼附体的教会和自己的老师主教大人在女孩的事情上唱反调,这个本已经被提名当选教皇在梵蒂冈图书馆管理者的优秀神父,在爱情来到他身上时,表现出了和狂犬病感染者一样的失控与无畏。 当徳劳拉的爱被教会发觉后,他被剥夺了一切头衔和圣职,医院为麻风病人洗澡来赎罪,他毫无怨言的干着这极具感染风险和侮辱的活计,因为爱让其内心早已明白,此生除了席尔瓦,便什么也不会再缺。 终于,徳劳拉通过修道院的秘密地道潜入席尔瓦的牢房,用一起读为宗教所禁忌的诗歌与缠绵的热吻,一夜夜与这个十二岁的女孩私会,而席尔瓦也爱上了这个为自己放逐了一切的三十六岁男人,他驯服了一个因被抛弃和野蛮生活而不羁的魔鬼,而她则唤醒了一个因一生压抑在顺从中而爆发的野兽,他们在情欲的泥潭中打滚,以爱情的名义,抒发着各自对这个世界无边的仇恨和绝望。 而主教并没有因弟子的误入歧途而放弃为女孩驱魔的大业,当他体弱的身体刚刚好转,就投入到这份上帝的工作中,席尔瓦被驱魔意识折磨的不成人形,铜色的长发也被剃掉,在她声泪俱下的向徳劳拉诉苦的那一夜,成了他们没有准备的永别。 因别的犯人通过修道院的密道出逃,这个连接他们唯一的途径被彻底封死了,那一夜,徳劳拉把两只手都挖烂了,也没能打穿封住地道的那堵墙,席尔瓦最终没能弄清爱人出了什么事,而徳劳拉则清楚的知道,他愿为其而死的挚爱,此时正在经受驱魔仪式非人的折磨。 五月二十九号这一天,因疑似狂犬病被父亲再一次抛弃,囚禁入圣卡拉拉修道院的她,至始至终没有表现出任何感染和发狂的迹象,但在准备为她进行第六次驱魔时,发现她已经为为爱死在了床上。 终究杀死席尔瓦玛利亚的不是狂犬病,而是爱情,更是对爱情的等待和折磨,她曾经问过父亲:“爱情真的可以战胜一切吗?”侯爵回答他的女儿:“当然,不过你最好别信。” 本书中的宗教裁判所和驱魔仪式,就像是今天社会一只对爱情野蛮控制和定义的手,得到社会认可的才是爱情,不被认可的就是魔鬼,在既定形式下循规蹈矩的就是爱情,对抗这个傻瓜系统和统一化道德标准的则是魔鬼,每个人都渴望爱情,而大多渴望的是一种没有代价、有别人的经验作先例和指导的爱的模式,但却忘记了,爱情是一种违背天性的感情,它把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带进一种自私的、不健康的依赖关系之中。我们不理解爱情和我们不理解上帝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两者是一种带着纯洁追求而又受制于贪婪本性的被选择之无奈,我们渴望上帝但又不想付出接近他的代价,就躲在系统化的宗教中自欺欺人,任何企图挑战被人所制造和规范的信仰体系,都是在试图挑战一个没有人愿意醒来的梦,即使离真正的上帝越来越远,我们也习惯了在这场梦中自称虔诚,因为真正上帝的保护还依然是一场虚无的许诺,而宗教对形式主义虔诚的认可却是实实在在的虚荣,安享在这场虚荣的幻光中,我们拒绝求变,拒绝科学,拒绝一切我们念念有词、口口声声的上帝的旨意,去神格化我们屡试不爽的懦弱,去妖魔化我们抱有畏惧的冒险。在这里我想到了《爱在瘟疫蔓延时》里的一句话——“安全感、和谐、陪伴和责任这些东西一旦相加,或许看似爱情,也几乎就要等于爱情,但它们终究不是。”当社会把爱情也概念统一为一个如信仰一般的体系,赋予本应该单纯的它本不该具有的部分,爱情就变得像是一个宗教,侯爵和席尔瓦说爱可以战胜一切,但最好别信————一个我们带着对爱情的简单渴望开始的,却因它的巨大不确定性和残酷代价转而建立的一个和它毫不相干的庇护,来骗大部分人我们有能力去爱也正在被爱,因为没人敢于承认孤独。 叶书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falanxibaoa.com/flxbzx/7064.html
- 上一篇文章: 单招综合技能测试题库道参考题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